美国19世纪30年代,市场革命和西进运动创造了一个令欧洲来访者颇为惊讶的社会:它充满活力、物质丰富、时刻处于一种马不停蹄的动态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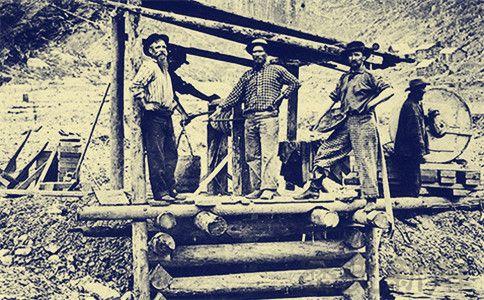
图 西进运动
1835年,英国作家哈里雅特·马蒂诺(Harriet Martineau)来到芝加哥,看到街道上“挤满了土地投机者,从一个销售市场急匆匆地赶往下一个……当我们同行的男士走在大街上时,店铺主人会从铺面里向他们致意,推销农场和其他各类形式的地产,劝说他们在土地价格抬升之前要敢于冒险投资”。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也对美国人那种按捺不住的充沛精力和明显的不愿在一个地方久留的做法印象深刻。“当你一踏上美国的土地,”他观察到,“你会发现自己立刻被卷入某种急速不停的骚动之中。你周围的所有一切,都处于动态之中。”西进移民和城市的发展创造出一个巨大的、不再与地方社区相连接的流动人口队伍,移民们都想抓住经济变化带来的机会。“在美国,”托克维尔写道,“一个人建造一幢房屋,打算在里面安度晚年,但在房子封顶之前,他已经把房子卖掉了;他在花园播种,种下的树刚刚开始结果,他已经把园子出租了;他把一块荒地开垦出来播种,地里庄稼的收获却是由其他人来完成的。”
西部与自由
西进运动和市场革命深刻地影响了所有美国人的生活。它们强化了某些旧的关于自由的认知,也创造了一些新的自由的理念。例如,美国自由长期以来是与获取西部土地的可能联系在一起的。纽约的新闻记者约翰·奥沙利文(John L. O'Sullivan)首先使用了“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这句短语,意即美国负有一种毋庸置疑的、神谕的使命:即要占领整个北美大陆。他宣称道,相对于国际条约、发现的权利和长期的居住历史等理由而言,美国人拥有远比所有这些更具说服力的权利来占有西部领土。美国人对北美大陆的占有权来自于美国拥有的历史使命,即要扩展自由的疆界。奥沙利文写道,其他人的理由必须给“我们的天定命运”让道,我们注定“要遍布和拥有整个大陆”,它“是上苍赐予我们用来进行关于自由的伟大试验的”。那些挡住我们进行扩张的人——英国和西班牙这样的欧洲强权、土著美洲人、墨西哥人——都将是自由进步历程中的障碍。
奥沙利文是在1845年写下这些话的,可天定命运的思想早已为人所熟知。当移民人口翻越了阿巴拉契亚山脉时,西进运动与自由的联系也一同翻越了山脉。“自由女神”,肯塔基的国会参议员约翰·布雷肯里奇(John Breckinridge)宣称道,不受“地理局限的控制”。一种空间上的开放感越来越变成美国自由的一种中心内容:无穷无尽的机会不断涌现,只要对幸福的追求需要这样做,人们随时可以打点行装出发,奔向新的地方。与他们的先行者一样,这一代美国人也坚信,美国是上帝选择的人类历史上争取自由的最伟大的试验,西进运动是这场天定命运的一部分。法国历史学家米歇尔·切瓦里尔(Michel Chevalier)是19世纪30年代众多访问美国的欧洲人之一,他写道,美国自由既是一种“现实的思想”,又是一种“神秘的思想”——它意味着“一种行动和运动的自由,美国人则利用这种自由在上帝赋予他的这片广阔领土大肆扩张,并将其征服为自己所用”。
在美国民族的神话与意识形态中,正如华莱士·斯特格纳(Wallace Stegner)后来所说,西部将作为一种“生而自由的美国人所拥有的最后家园”长存下去。在西部定居和对其经济资源的剥削,使得美国避免重走欧洲的老路,避免成为一个社会阶级固定不变、拥有大批赤贫的工资劳动力队伍的社会。在西部,土地比较容易获得,压迫性的工厂体制较为少见。随着原始州内的人口增长和土地价格上涨,年轻人想要获得一块土地,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农场主的希望变得逐渐渺茫时,西部仍然为获取经济独立保留了机会,而经济独立是享有自由的社会条件。

超验主义者
躁动不安和竞争性强的市场革命也推动了美国自由与另外一种东西相互认同,那就是,自主的个人在追求经济成功和个人发展时不应受到节制。当地的“一个重要的革命”,哲学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在19世纪30年代写道,是“个人的新价值”的出现。供个人发展的新机会对杰斐逊的“追求幸福”下了新的定义,这个定义非常适用于当时的社会,因为传统的空间和社会界限已经被领土扩张和市场革命所摧毁;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流动、从一种地位到另一种地位的改变,已经成为美国生活中的通行特征。
在1837年发表、后被多次重印的名为《美国学者》的演讲中,爱默生呼吁,处于写作和思考的人要“感觉到自己所有的信心,……从不要为大众舆论所压倒”,寻找到并相信自己的“自由定义”。在爱默生的定义中,自由不是一堆事先存在的权利和特权,而是一种自我实现的开放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个人可以重新塑造自己和自己的生活。这个时代的主旨,他宣称道,是“赋予个人的新的重要性”和个人的“解放”,这就是“美国思想”。
爱默生也许是新英格兰地区一个称作超验论者(Transcendentalists)群体中最为著名的成员。先验论强调,个人判断与既存社会传统和体制相比更为重要。爱默生在马萨诸塞康科德的邻居、作家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对爱默生关于相信自我的呼吁做了回应。“凡相信自己比邻居更正确的人,”索洛写道,“都拥有一票的多数。”
个人主义
这个时代的“个人主义”(这个词在19世纪20年代才进入美国词汇)也充满了讽刺意味。尽管市场革命推进了相处遥远的人们之间的商业交往和联系,“主权个人”(sovereign individual)的思想则宣称,美国人不应该依赖他人,而应做到自食其力。自然,个人的独立自主早就与美国自由联系在一起。然而,18世纪思想家们并不认为个人的私有幸福与负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公共道德(被定义为对公共福利的献身精神)之间有任何矛盾之处。而此刻,托克维尔观察到,个人主义“导致社会中每个成员割断了与他的同胞群体的关系,与家人和朋友相分离……基本上听任社会的自生自灭”。美国人迅速懂得了自我的世界——这在后来被称作是“隐私”——是一个无论是其他人还是政府都无权干涉的领域。如同在下一章将要讨论到的,个人主义也激发了民主的扩展。对自我的拥有而不是对财产的拥有,使得个人具备了行使投票权的能力。
当他在19世纪80年代回首往事的时候,爱默生把内战前的时代视为一个“社会存在”让位于“个人独立自主增强”的时代,个人“……疯狂地在他本身发现自己的资源、希望、奖励、社会和神性”。梭罗则以自身的生活实践诠释了爱默生的观点:在政治、社会和个人等问题上,个人的良知占有最重要的地位,每个人需要在这些问题上寻求自己的道路,而不是一味的随大流。与其他的先验论者一样,他并不赞同个人在市场社会中追求幸福的方式。梭罗认为,现代社会将人变成了“他们手中工具的工具”,扼杀了个人的判断能力;发财致富的目标使人们鬼迷心窍,并将他们围困在单调乏味、令人窒息的工作之中。即便是在“这个相对自由的国家”中,他写道,大多数的人都为物欲所累,没有时间来欣赏大自然的美丽。
为了摆脱这种命运,梭罗退回到康科德附近的瓦尔登湖隐居了两年。在那里,他可以与统治美国社会的“经济和道德专制”实行隔绝,享受孤独的自由。后来他发表了《瓦尔登湖》一书。这是一部自我经历的记述,也是一种对市场革命的批判,在他看来,市场革命正在贬低美国人信奉的价值观,破坏美国的自然环境。一片曾在他青年时代为树林所覆盖的土地已经为伐木工和农场主砍伐得面目全非,几乎不再剩下任何树林和野生动物。在书中十分著名的一段文字中,梭罗写道,他对自然的欣赏为远处传来的一辆火车头的汽笛声所打搅——这说明,要想逃避市场革命已经变得如何地不可能了。梭罗呼吁美国人“简化”他们的生活,不要为积累财富所钱迷心窍。他坚持认为,真正的自由是埋藏在个人内心深处的。
第二次大觉醒运动
在第二次大觉醒(Second Great Awakening)中,席卷全国的宗教复兴给个人改良、自我依靠和独立自决等思想注入宗教的色彩和支持。这些复兴活动始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最初由负有盛名的宗教领袖组织,他们为这个年轻共和国出席教会活动的人数之少(18世纪90年代,约有10%的美国白人是定期参加教会活动)深感不安。然而,复兴活动很快蔓延到了现存教会的范围之外。19世纪20年代末至19世纪30年代初,当查尔斯·格兰迪森·芬尼(Charles Grandison Finney)在纽约州北面和纽约市举行数月之久的复兴大会时,宗教复兴活动达到了高潮。
芬尼是康涅狄格农场主家庭的儿子,1821年他在参加了一次宗教复兴会议之后,受到激发,决心参与复兴祈祷。如同18世纪中叶的第一次大觉醒(见第四章的讨论)中的旅行布道者们一样,芬尼使用非常生动的语言来描述地狱的情景,同时向那些放弃了罪恶行径的改信者提供获得拯救的承诺。他在纽约州北部的奥奈达县(Oneida County)布道获得成功之后,成为一个扬名全国的明星。在芬尼的布道之后,一份报道这样写道:整个地区“完全彻底地被圣灵所推翻了”,这里的“戏院被抛弃了,酒店也变得圣洁了……人们在祈祷时表现出一种更为高尚、更为纯真的虔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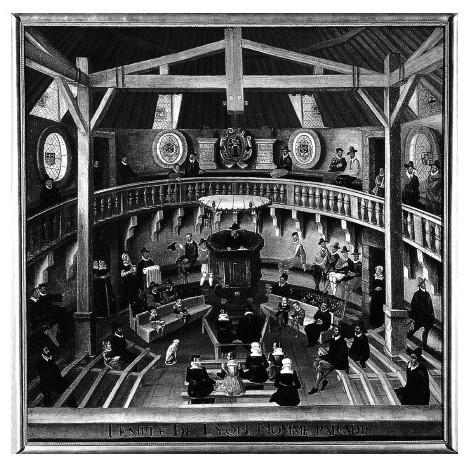
图 第二次宗教大觉醒
第二次大觉醒也使美国基督教变得更为民主化,使之成为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众运动。美国独立之时,在美国布道的基督教牧师不到2000人。1845年,这个数字达到了4万人。类如卫斯理派和浸礼派的福音教派教徒人数出现了爆炸性的增长,各种小型教派也四处传播和蔓延。到19世纪40年代,卫斯理派拥有100万教徒而成为美国最大的教派。自然神派对体制化的教会一向抱有敌意,曾在建国之父那一代人中十分盛行,此刻它却逐渐隐退,基督教较之从前更成为美国文化的中心内容。托克维尔写道:美国人“在他们心目中将基督教和自由如此亲密地糅合在一起,要让他们只是理解其一而不理解其二是不可能的”。
新的宗教预言家在19世纪早期定期的出现,用小说家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的话来说,他们决心要“用福音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大型的户外布道会在边疆地区尤为盛行,在这些布道会上,充满激情的福音布道家们拒绝接受人生而具有原罪并逃脱不了预先设定的命运的思想,他们鼓吹人类拥有自由意志的教义。在这样的聚会上,富人与穷人、男人与女人,有的时候甚至白人与黑人,肩并肩地在一起祈祷,保证放弃带有世俗罪恶感的生活,接受上帝指引的生活方式。
大觉醒的影响力
相对于几十年前的第一次大觉醒,第二次大觉醒更加强调个人在精神事务上做出判断和选择的权利,强调通过信仰和善举来获得普世拯救的可能性。每个人,芬尼认为,都是一个“道德上的自由意志者”,即一个人能够自由的在基督教生活与罪恶生活两者之间进行选择。犯有罪恶的人可以“改换心灵”,接受精神自由;而这种自由,用福音派牧师乔纳森·布兰查德(Jonathan Blanchard)的话来说,指的是“耶稣对那些自由和自愿选择服从他的理性的个人所进行的一种完全的统治”。
复兴运动的牧师们抓住市场革命带来的机会来传播他们的信息。他们筹集资金,通过运河、蒸汽机船和铁路等运输线开展漫长的祈祷旅行,并把批量生产、廉价制作的宗教小册子散发到全国各地。复兴主义者将宗教向大众开放,鼓励群众的参与;他们的布道强调,普通美国人都可以决定自己的精神归宿,这一切可以说与正在迅速蔓延的市场价值观是相辅相成、异曲同工的。
当然,福音派牧师们并非都是市场社会的鼓吹者。事实上,他们经常将贪婪、自私自利以及对他人的生死福祸所表示的冷漠作为罪恶来谴责。芬尼把“自私”——一种在市场革命的推动下、不顾一切地为聚敛财富而采取的个人主义的极端形式——称作“撒旦帝国的法律”,不是上帝的法律。复兴运动在市场经济扩张最为迅速的地区发展最快,如沿着伊利湖的上纽约州地区。芬尼在这一地区的追随者大多为商人和职业人士。福音派牧师把一种节制的个人主义当成自由的要素来推行。他们将勤奋、持重和自律等当成自由选择的道德行为的典范,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也在推进那些在市场文化中获取成功而必备的基本素质。
